- 资料正在整理中!

在公益的江湖里,一直存在着一条心照不宣的“鄙视链”;或者说,是一道因“出身”而划开的巨大鸿沟。

我是福建省正能量公益服务中心的创始人,目前担任中心工会主席,并曾连任第一、二届理事长。在公益这条路上,我深耕了十三年。
十三年来,我个人为这个机构垫付了多少办公经费和运营成本?粗略一算,打底一百万。我不是富豪,这每一分钱都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,砸进这份我视为生命的事业里。我和无数民非(社会服务机构)的同行一样,是被现实的“三昧真火”日夜炼熬,却始终不肯散架的汉子。
今天,我就是要用这身被真火炼过的骨头,戳破公益圈里那层虚伪的窗户纸。
关于打底一百万,我补充一下:我说自己垫付了十三年,累计不下百万,哪怕如今坦然说出来,依然鲜有人信,甚至不乏质疑的声音。可试想,一个机构刚刚成立,没有群众基础,没有社会公信力,前期的每一步、每一关,几乎全靠创始人咬牙硬撑。这十三年,如果拆开来算,平均每个月垫进去五六千不止。试问,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投入,有没有打底一百万? 项目经费不够,想办法补上;运营出现缺口,一次次自掏腰包填平。公益不是一句口号,它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付出,是看不见的汗水,是数不清的深夜独自承担的压力。 这条路,我走了十三年。而这打底的一百万,不是数字,是青春,是信念,是我对公益这两个字最倔强的回答。(在这里,我要感谢第一、二届的理事以及“护巢计划”的爱心守护者们,在机构的发展历程中,你们也曾义无反顾的捐赠办公经费支持过,没有你们机构发展更加艰难。)
一、公益三国杀:生而不同的“命”与“病”!
中国的公益生态,看似百花齐放,实则是三个世界,三种活法。

1.先说“社团”。许多社团,好比是“有祠堂的宗亲”。他们有相对稳定的会费收入,如同有一片薄田租子,虽然发不了大财,但至少饿不死,能维持基本的体面,有精力去搞搞活动,维系圈子。他们的焦虑,往往是“如何发展得更好”。
2.再说“基金会”。特别是那些企业基金会。他们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“正规军”。背后有母体企业每年稳定的巨额捐赠,项目款、人员工资、豪华办公室的租金,全都打包在捐赠里。他们的秘书长,核心工作是“花钱”和“管理”,是优雅的“资源分配者”。他们从未体会过,明天就要发工资,而账上只剩三位数的绝望。
3.最后,就是我们“民非(社会服务机构)”。我们是公益界的“孤勇者”和“乞丐”。我们没有会费,没有母体企业输血,每一分钱都要靠向社会“化缘”。群众基础薄弱,捐赠时断时续。每一个项目款,都严格专款专用,想从中抠出一点办公经费,比登天还难。民非的创始人,哪一个不是集“理事长、筹款人、会计、司机、搬运工”于一身的“十项全能”?我们不是在做事,我们是在“求生”。太多的民非,全靠创始人或理事长以一己之力,用个人的积蓄(甚至拆借)和情怀,苦苦支撑着机构的门面不倒。这就是我们面临的、冰冷而残酷的现实。
二、段位天壤之别,谁给你的勇气来“教书”?
正因为三者从诞生之初就拥有截然不同的“血液循环系统”,其掌舵人无论是会长、理事长还是秘书长所面临的生存课题与核心能力要求也全然不同。其能力维度、生存哲学和人生体验也有着云泥之别。
一位依托母体企业每年固定捐赠的基金会秘书长,他的核心能力或许是项目管理和品牌维护。他无需为明天的办公租金和员工的下月薪资能否发出而彻夜难眠。
一个从未为钱发过愁的基金会秘书长,来教导一个每天都在“找米下锅”的民非(社会服务机构)亦或是社团创始人“如何做战略规划”,这无异于一位住在宫殿里的王子,对着田里耕作的农民大谈“稼穑之美”与“园艺修剪”。
荒唐!可笑!
而一位民非(社会服务机构)亦或是社团的创始人,他首先必须是“求生专家”。他得是筹款人、项目执行者、会计、文案,甚至是保洁员。他每天都在“找米下锅”,他的“段位”是在一次次断炊的危机中,在一次次为爱发电的疲惫里硬生生磨砺出来的。
所以,当我们看到一些基金会动辄组织“公益讲堂”,高高在上地教导我们这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民非(社会服务机构)以及社团“该如何做事”、“该如何做项目”、“该如何专业化”时,我们感到的不是茅塞顿开的欣喜,而是一种强烈的荒诞与不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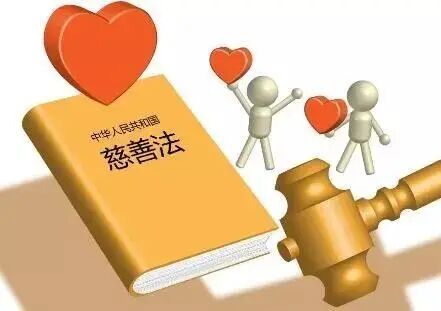
你们高谈阔论“专业化”、“项目化”,可曾知道,我们连聘请一个全职专业人员的办公经费都无处列支?你们设计的那些复杂精美的逻辑框架,可曾考虑过我们连执行的人都请不起?
这像极了古代那个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故事。一位从未饿过肚子的人,对着饥肠辘辘的百姓大谈烹饪肉粥的技巧。
你们的“段位”,是建立在庞大而稳定的资源基础之上的。我们的“段位”,是在一次次断炊危机中,靠个人血肉之躯硬扛出来的。
三、真英雄,敢不敢下场走一遭?

我们并非拒绝学习,我们渴望成长。但我们敬重的是那些真正经历过战火、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老兵,而不是只在沙盘上推演过兵法的理论家。
有本事,贵基金会的运作不是靠背后母体企业的固定捐赠。
有本事,请贵基金会的秘书长靠自身的筹资能力,去完成每年动辄数百万的筹款目标,并能从中合理地支付多名全职员工体面的薪资与充足的办公经费。
若您能办到,您走过的路、踩过的坑,字字珠玑,我们必定洗耳恭听。
若您办不到,仍享受着每年母体企业固定捐赠的安稳与优越,那么请您收起那副“好为人师”的嘴脸。这种脱离地心的“指导”,除了满足您的虚荣心,对在泥泞中前行的我们毫无益处,甚至是一种傲慢的伤害。
公益的生态,需要的是共生与共情,而不是俯视与说教。请多一些真诚的携手,少一些居高临下的布道。先理解我们的“饿”,再來谈论我们该如何“吃好”。
四、我在此,想向那些高高在上的“导师们”发出一个最直接的挑战!
请问,哪位基金会的秘书长有胆量辞去现职,自己从零开始,去注册成立一个全新的基金会?
而且,这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开办资金不是靠母体企业施舍,不是靠父辈资源,全靠你赤手空拳向社会募捐而来。
如果你能做到,在你为新机构的生存熬白了头,在你为员工的工资求爷爷告奶奶,在你为自己的理想垫尽最后一分家底之后,你再来站在我们面前。
到那时,你无需多言,你本身的存在,就是一部最好的教材。你吐出的每一个字,我们都奉若珍宝,俯首倾听。如果您做不到,就请闭上那张“好为人师”的嘴!请收起那套不接地气的理论!你们享受着母体企业捐赠资金带来的庇护,却来嘲笑在风雨中衣衫褴褛的我们姿势不美,这不是指导,这是一种残忍的傲慢,是公益版的“何不食肉糜”!

寄语民非(社会服务机构)与社团:你们是这土地里倔强的根!
说了这么多难处,揭了这么多伤疤,我们或许会问:既然这么难,为什么还不放弃?答案,就写在每一个民非(社会服务机构)和社团同仁那被汗水与泪水浸透的初心之上。
因为我们见过受助孩子脸上重新绽放的笑容,足以抵消所有奔波的疲惫;
因为我们听过孤寡老人那句“你们来了真好”,瞬间抚平了万千委屈;
因为我们相信再微小的善念只要持续闪耀,也能驱散一片黑暗;
因为我们执着于一个最朴素的愿景:让脚下的这片土地,因为我们的存在能再多一点点的美好与温暖。
正是这份愿景成了穿透现实阴霾的光,成了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全部力量。所以在此,我要向所有在困境中挣扎前行的民非(社会服机构)和社团致以最崇高的敬意!
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伟大。你们没有金光闪闪的铠甲,却用血肉之躯为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筑起了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。你们是公益生态里最坚韧的“毛细血管”,深入肌体末梢输送着最基础的养分。
你们的坚持,是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,一曲关于理想与信念的嘹亮凯歌。

请不要因为资源的匮乏而看轻自己。你们在极限条件下展现的创造力、执行力和生命力,是任何坐在空调房里的理论家都无法企及的“真本事”。
前路或许依然漫长且崎岖,但请记住,你们从不孤单。福建省正能量公益服务中心与你们一样,是同在这条路上跋涉的同行者。我们理解你们的每一个难处,也敬佩你们的每一分坚持。
未来,让我们继续在一起,一起走。让我们彼此照亮,互相温暖。在质疑声中互为臂膀,在至暗时刻互相点灯。我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,就是一片星海;我们的声音共鸣在一处,就是惊雷。
愿我们这些倔强的根,终能穿透坚硬的现实,让公益的森林枝繁叶茂,万古长青。
结语:
公益的土壤需要的是共情、携手的肥料,而不是居高临下的除草剂。我们民非(社会服务机构)和无数挣扎的社团不需要空洞的说教,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资源支持,对运营成本的尊重与覆盖,以及一份发自内心的、平等的理解。
十三年的火,烧掉了我的稚嫩与幻想,也炼就了我的硬骨与直言。此文,为我自己,也为所有在泥泞中依然仰望星空的公益同行而写。
诸君,共勉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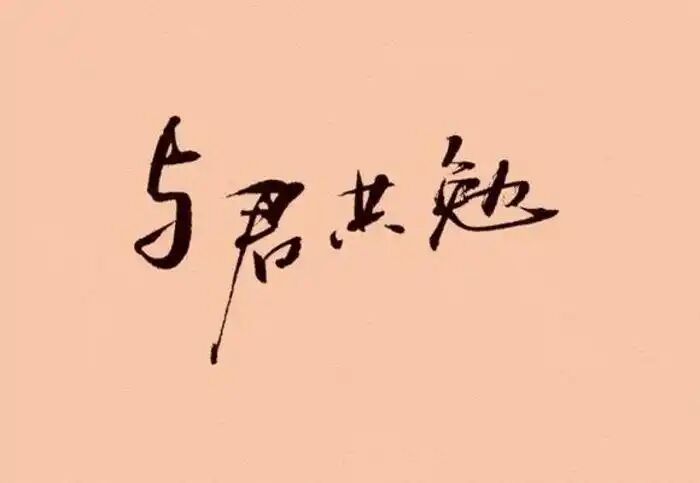
概念界定声明:
为确保本文讨论的精准性,特对文中核心概念进行界定:
1.本文所述“民非”:特指那些纯粹依靠社会捐赠、资源高度不确定的志愿型公益慈善组织。其核心特征为运营的强不确定性与对志愿性的高度依赖,本文的观察与论述均基于在此类组织中的实践经验。
2.不涉及的范围:同样注册为“民非”的、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、社工按劳取酬的专业社工机构,其运营逻辑与资源模式与本文探讨的范畴存在本质差异,故不纳入本文讨论。
3.关于“基金会”: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在公益生态中许多依靠自身能力筹资成立的草根型基金会,其生存与发展逻辑与本文所述的志愿型“民非”高度相似。但因其组织形态与功能定位及运作模式有所不同。为聚焦议题,本文的讨论不延伸至该类领域,以避免概念泛化。
以上界定,旨在使论述更为聚焦,并非对未提及机构类型的价值评判。恳请读者在上述框架下理解文意。
- 友情链接:微信公众号登陆页面 |
COPYRIGHT(C) POSITIVE ENERGY PUBLIC PLATFORM
正能量公益平台 版权所有 闽ICP备13002196号-2
亿网行网络制作维护 腾媒大数据营销推广支持
电子邮箱:chengui@znlcn.org


 手机扫一扫
手机扫一扫